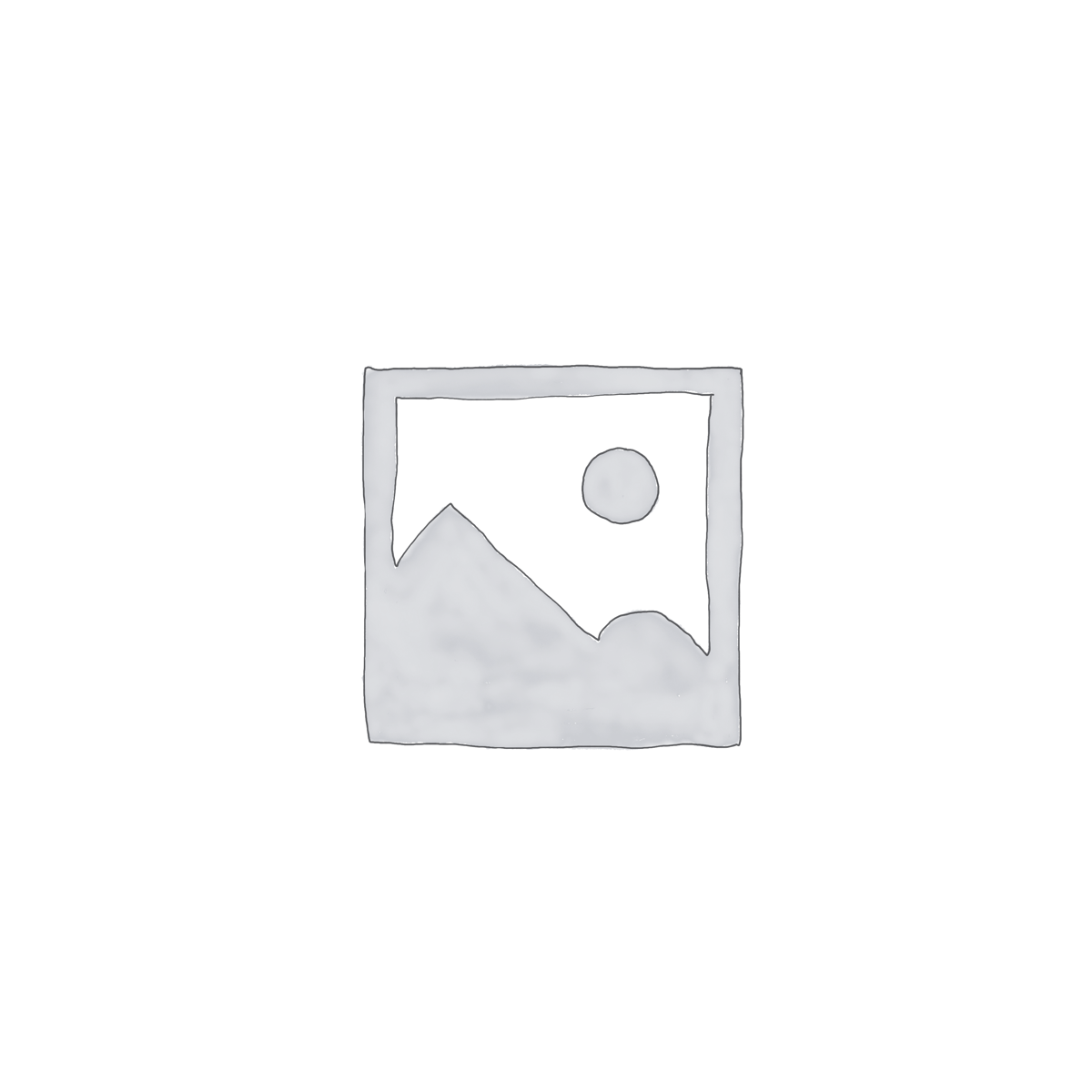requestId:68a75741839429.10357488.
政教相維下的“兼體分用”:儒家與中國傳統的文教政治
作者:任鋒
來源:《學海》2014年第五期
時間:甲午年閏玄月廿九
西歷2014年11月21日
摘要:對于中國政治次序中政教關系的懂得,應擺脫二十世紀以來宗教化、意識形態化與知識化路徑的限制,反思政教一元/二元、政教分離/合一等論說的格式缺點。“政教相維”下的兼體分用,一方面指出儒家中國的文明設定中政治與學教持有統一個意義和價值的次序,構成一個整體的天生維持結構,同時二者之間經由分歧的次序氣力得以表達,其間有效能和機制的分工或分化。由此構成的文教是一種公共事理意義上的最基礎精力形式,既非東方文明語境中的宗教,也不是與現代“主義”政治配套的意識形態,更不是單純的學術知識這一感性化情勢。政教相維制體現出儒家思慮次序構成的獨到精力。
關鍵詞:政教相維;儒家;文教;管理;公共
現代中國人思慮身處此中的次序轉型之際,很不難將東方現代確立的政教形式作為一個理所當然、甚或是不言自明的主要指標。伴隨著這種教條化認知的趨向,也逐漸衍生出處理中國文明傳統的類似心智:即無論瑜伽教室褒貶,大師把儒家作為西式宗教對待,從而根據各自對于現代次序的典范想象,提出現代中國的政教分離抑或透過設立國教而達成政教合一。
筆者認為,這種教條化及宗教式的認貼心智需求反思,我們需求從一種文明比較的廣闊視野來從頭懂得和表述政教關系這一最基礎命題。現有的風行概念,無論政教合一、政教分離,或許是政教一元、政教二元,能否為認定中國文明次序類似問題的恰當表述情勢[1]?從次序構成的角度來看,該若何掌握政教關系所指向的最基礎規則與管理體系之間的復雜機制?儒家傳統能帶給我們何種文明啟示,這種啟示對于現代中國次序重建的前路有何珍貴價值?這些相當主要的追問,或許能幫助我們進一個步驟把經驗現象問題化,進而沖破教條化的盲區,推進當前的相關討論。
一、宗教化、意識形態化、知識化路徑的反思
自晚清進進轉型時代,中國人在思慮政教關系時,對于代表“教”之一維的儒家傳統呈現出三種分歧類型的路徑,深入影響了進一個步驟的政教解釋和實踐形態。這三種路徑,分別呈現為宗教化、意識形態化與知識化。
宗教化的路徑,乃是受東方宗教文明與現代性的啟發,運用宗教的范疇來從頭懂得儒家傳統,并據此范疇重建現代轉型過程中儒家所應具有的組織形式及其與當局、社會各組織之間的關系形態。這個路徑,從儒家本身轉型來看,可以說具有強勁的吸引力,也形成了最顯凸起的影響力。自清末平易近初以來的康有為、陳煥章,降至晚近儒家復興海潮中的蔣慶諸賢,都在這條路徑上支出了艱辛的盡力。
以康、陳等人設立儒教會為例,這個路徑的關鍵環節在于論證儒家的宗教本質、樹立新的組織形式。他們既然認定了宗教形式這一轉型路徑,同時明了東方基督教式宗教的義理和組織特質與儒家傳統存在相當差異,是以嘗試采取一個廣義的、寬泛的、擴展式的宗教觀,將儒家解釋為一種中國獨有的特別宗教(如陳煥章語“文明之宗教”)。好比認為孔教并重人性與神道、并尊天主與祖先、對其它崇奉的包涵涵化,并從情勢和效能方面盡力證成孔教與普通宗教的相通性,如陳煥章對于孔教教主、名號、衣冠、經典、信條、禮儀、鬼神、魂學、報應、傳布、統系、圣地和廟堂的認定[2]。
他們在軌制譜系上盡力唆使出這種組織創新的傳統依據,如陳煥章于1912年10月儒教會成立年夜會上自陳,“相與創立儒教會,以講習學問為體,以救濟社會為用,仿白鹿之學規,守蘭田之鄉約,宗祀孔子以配天主”[3]。但是,對于這種組織變遷的創新性和斷裂性,他們本身是有明確自覺意識的。將孔子由先師、圣人塑造為教主、年夜立法者,采用“孔子紀年”,強調國教形式,移用西式政教觀從頭解釋中國政治文明傳統,并賦予這一組織為新時代立心的精力任務(如梁啟超所歸納之“進步主義”、“兼愛主義”、“同等主義”、“重魂主義”),這種出于今文經學精力的時代呼應顯顯露鮮明的創制意圖和轉型盼望[4]。
這種將儒家宗教化、國教化的思惟與組家教織盡力,與康有為等人的政治宏圖緊密配套,在晚清為維新改制營造思惟基礎,在平易近初則與虛君君憲互通款曲。從一種憲制轉型的角度來看,儒家宗教化不僅被視作無益于凝集新造國平易近的文明和政治認同,也為政治配合體維系了一個堅實的品德和精力基礎,為確立穩固的公共政治權威供給倫理支撐,并且可承順傳統而與現代社會多元不受拘束的崇奉訴求并行不悖。
從歷史命運來看,康有為等人的這個路徑遭受到了很年夜的艱阻和窘境,結果遠低于預期。艱阻之緣由,很年夜水平上來自于宗教化路徑所引發的儒家傳統內外之質疑挑戰。盡管采用了較具彈性的擴展式宗教觀,儒家宗教化的解釋仍難以獲取謹記傳統價值之人士的內在認可,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的批評可謂代表了時人的一種主流態度[5]。而從內在于儒家的立場來看,如若儒家是宗教崇奉,則或許認為宗教乃時代私密空間落后守舊之象征,或許認為國教化有悖于現代崇奉不受拘束的原則,潛在地不益于多崇奉族群之政治團結。而在實踐層面,當儒家相繼掉往科舉制、士紳組織、君主制等舞蹈場地有機憲制支撐后,若何透過宗教化渠道而進進蒼生日用常行,在與既有宗教的競爭中安身腳跟,這一軌制化挑戰并未獲得無力的應對。
公允地說,儒家宗教化的路徑顯示出傳統精勇敢于變革、開放進取的創制精力,并且能夠結合儒家傳統的本身特點自覺地往尋求一種擴展了的宗教文明視野。這種路徑不掉為傳統轉換的一條可摸索性思緒,其實踐能量也并未獲得充足檢驗。但是,這種現代自覺,最基礎上依然是一種有待充足發展的文明自覺。殆因其固執于對于西式現代文明的宗教性認定,而中國文明本位的自覺未必必定要循取西式宗教的格局。我們瑜伽教室完整可以不用自我設限,而從儒家傳統的特質出發往掌握一個更適宜歷史與文明特征的政教形態。這般,才能夠既獲得謹記傳統價值之人士的內在認可,又擺脫從宗教視角強調所謂崇奉不受拘束多元的理論羈絆。
中國現代轉型過程中,儒家經歷的第二類政教性轉換體現在意識形態化的路徑之上。所謂意識形態化路徑,其實質在于將一個開放、多樣、有機的文明精力傳統抽象轉化成為了一種精力靈性上封閉顓頊的派性話語或謂黨派話語。
這個路徑的現代緣起,聚會場地或許同樣可以在康有為等人為政治宏圖供給理論兵器的教義學盡力中發現眉目。康南海充足應用公羊年齡學激活并擴充的很是可怪之論,以一種挑戰并扯破彼時文明政治共識的戰斗姿態掀開了現代中國精力變遷的巨幕。與傳統中歷代年夜儒如董子、王安石重組儒學資源以謀革政分歧,南海的這種話語營造大量量引進東方元素,并勇于判真偽、鑒高低,其所形成的話語影響已年夜年夜溢出儒家傳統所一時整理之范圍。從改制論激而涌起守舊論、反動論,以反動主義為表征的意識形態時代遂籠罩了二十世紀以來之中國精力,而新文明運動之斫喪傳統只是這一時代巨靈的顯赫象征之一[6]。
而儒家傳統,更是在這一意識形態巨流中首當其沖,深深墮入一種反題絕境。筆者曾指出這個反題絕境,就是國人一方面將現代文明的標志泊定于平易近主和科學,另一面將儒家傳統解釋為阻礙現代文明的專制與科學,從而墮入必先自噬方得自救的悖論和絕地。儒家傳統在這個意義上被塑造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同義詞,被誤解為、臭名為維護封建田主階級最基礎好處的統治意識形態[7]。這種極端單面化的抽象認定,自己又是激進精英階層本身實現政治動員、凝集戰斗氣力的政治話語之歷史—實踐觀基礎。換言之,儒家被高度地政治意識形態化,這同時又構成現代中國敏捷走向意識形態政治的一個主要環節。
這種意識形態化的路徑并非儒家本身調適選擇的結果,而是在政治激化怒潮興起下所遭遇的重整與再編。其構成機制相對超離了儒家所養成的文明經驗世界,在諸種具有激進性政治和文明情懷的特別氣力推動下,為了某些特定的實踐目標而強力塑造出某種系統性、排擠性的派性話語,此中包括了對于傳統精力因子的移用、替換或扮擬共享會議室。封建專制主義,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新舊平易近主主義、科學主義、反動主義、不受拘束主義、平易近族主義,構成包括宏大沖突性、對抗性的意識形態鏈條,氤氳滋長出至今仍魅影憧憧的意識形態豪情[8]。
意識形態競爭或許是人類精力告別古典心智進進現代文明的一個主要表征,有其必定之理勢。但是儒家之意識形態化路徑的特征,表現為在一個強烈批評傳統文明、全盤反傳統的脈絡中展開。能夠從社會機制、義理格式上維系良序競爭的共識框架被侵蝕殆盡,主義心態劫持經驗感性,批評解構湮沒技藝感性,意識形態競爭極易走向惡化、極化。這種意識形態豪情無助于養成穩健積極的公共人格,也晦氣于構成成熟有序的政治生涯。諸種主義對于儒家傳統雖有各種移用、替換,卻不克不及從最基礎上繼承儒家對于中華文明傳統善繼善述、損益維新的聰明,這是我們反思過往儒家之意識形態化的一年夜關節。
與前兩者互有交集,儒家在現代經歷的第三種政教性轉換表現為知識化、學術化路徑。假如說私密空間宗教化和意識形態化路徑尚能表現出強烈的精力共享空間維新訴求,那么第三種路徑更多地預示著精力和實踐訴求波折下的感性支離與高度情勢化。
之所以說交集,是因為在宗教化路徑中,同時也存在著對于儒家著眼于學統和知識實質上的年夜規模重編。這一知識化依然是內在于儒家傳統而生發的,相當水平上繼承并晉陞了傳統文明精力的訴求。而意識形態化路徑下的知識化過程,與前者有年夜分歧。由于該路徑會議室出租的歸宿乃是一種儒家文明傳統的倒像與反題,導致知識化路徑遂成為一個不斷的脫嵌和往魅。
這個意義上的知識化路徑是迷掉精力家園之后的感性流放,在精力和實踐標的目的上年夜多淪為意識形態政治的附庸。即以經學傳統在二十世紀的厄運來看,傳統中明經行道的旨趣最基礎上被否棄,湮沒不彰,導致經學一個步驟小樹屋步淪為歷史考古意義上的國故收拾,原來為經學涵攝指引的經世之學、義理之學、辭章訓詁之學也被割裂疏散到了從東方引進的各個現代學科之中[9]。由于掉往了與外鄉經驗文明相互說明解釋的智識紐帶,在年夜規模移植西學的過程中,這一知識化路徑一面陷儒學于僵逝世不生之地,一面在知識消化與現實次序構建之間形成深入的緊張甚至斷裂。反動主義意識形態政治下的整肅與閹割是一種變相的知識化處理,而標榜現代性下的學院化、知識分子化同樣是對儒家傳統的異化對待。
二、政教相維下的“兼體分用”:文教與管理體系
上述三種路徑,雖都能在傳統中發掘出必定的聲援資源,對于我們內在地掌握中國文明的政教基礎卻都有以偏概全之弊,或缺少充足自覺的文明特質意識,或受困于現代意識形態豪情的束縛。在其基礎,都不自覺地以東方政教形式(古典的與現代的)作為當然的基準,有待多元文明的反思檢驗。
有鑒于風行的政教分離/合一、政教一元/二元論述,前賢的一些分歧表述能夠幫助我們尋找反思的線索。如張之洞提出的“政教相維”,陳寶箴提出的“政教分途”,陳煥章提出的“政教并稱”,都沒有采用那種非此即彼、內在對沖的懂得格局,此中能夠折射出儒家傳統思慮這類問題的思維特質[10]。
“政教相維”所唆使出的相維相制思緒尤其能體現出儒家思慮次序構成的獨到精力。無妨以儒家經典《中庸》為例,首三句綱領云,“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子于《中庸章句》首章解釋中指出:“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天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克不及無過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于全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11]。這一段闡釋人類政治的來源,是觸及政治與品德精力、政治與至善之關系的年夜關節。
我們看到,儒家的政治觀以天道、天命、天理為最基礎條件,依此而懂得人的行為規則即所謂德性,而政治乃是基于對德性之節度而天生的立法立教事業。這里在性、道、教之間樹立起了相環而生的聯系,由以天則為基礎的德性,發展出以德性基礎的教、法。假如依其表述,政生自教,或謂政在教中。而這個教,乃基于天則為根源的德性規則。在這里,政治是內在于人類的品德行則之中,假如再引進“學”的維度,可以說政治是內在于圍繞品德規則的認知和傳習之中。此品德,不僅僅是心性修養層面的內在規訓,而是衍生于風俗平易近情、先例習慣、共識禮法的公共規則。這是懂得儒家文明中政學、政道、政教多重關系的基礎視野。
如程伊川解周易“觀”卦之《序卦》,“人君上觀天道,下觀風會議室出租俗,則為觀;修德性政,為平易近企盼,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可以說把天道平易近情性規則、規則化德性與德教式管理的邏輯闡明得非常清楚。伊川師長教師解彖辭曰,“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無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圣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全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天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全國服矣’”,解象辭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風俗而設政教也。皇帝巡省四方,觀視風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12]。這里唆使出,政教的本源恰是圣人代表的人類權威面對天人次序的敬畏、謙遜和節度,而政教本體依托的是基于天道風俗的禮法性規則及其倫理典範。
需求辨別的是,儒家懂得政治的年夜視野并非宗教式的,而是品德式的。這與儒家文明構成的天人次序特質密不成分[13]。
質言之,天人次序將中國人的超出精力充足內化于此世間的事物次序之中,自己并非一種張揚宗教性的意義次序。它并未汲汲尋求此岸世界的經營,也鮮有烏托邦主義的志趣,而在一種以經世為中間的實踐訴求下往安頓政治與人類德性規則的樞軸性關系。天人次序的這一特徵最基礎導引了中國文明從一種相維而非對峙的視角來懂得精力和管理事務。從基礎處,儒家消除了宗教安排下之世俗文明從分歧精力旨趣發展兩套并行之義理和組織體制的次序構想,而將以分歧方法維系超出精力的人間次序作為文明體的中軸。
進一個步驟,我把這種相維關系稱作為“合體而分用”,或如姚中秋傳授修改后的“兼體而分用”[14]。兼體分用,一方面說明儒家中國的文明設定中政治與學教乃持有統一個意義和價值的次序,構成一個整體的天生維持結構;另一面,二者之間經由分歧的次序氣力得以表達,其間有效能和機制的分工或分化。這樣一種關系,比較完全地體現出儒家次序構想的相維相制精力。
這樣的次序構想,可以說為我們呈現出廣狹二義的政管理解,二者都是以人類人間世中德性和管理規則為最基礎基礎。儒家強調在長期文明演進的基礎上,充足尊敬對于文明進化規則的繼承、收拾和提煉。所謂“學而時習之”者,所謂“天命之謂性”者,俱包容于此。依據這種體認,社會和文明精英飾演了規則發現者、表述者和踐履者的腳色,此是德之最基礎意思,也是普通所謂教化、向更廣泛范圍的人群示行、推廣規則的基點。這一層次構成了廣義政治觀的重心。而所謂狹義政治觀,是相對于前者,特指運用有強制力保證的管理方法(以政令刑罰為主)與相對倚重主體能動性的管理方法(禮樂),以后者優先的原則配合參與到前述文明進化規則的次序落實中往。廣義的政治觀把規則之發現、體認與教化都視為政治,狹義政治觀則強調多種管理方法、尤其是政刑的運用。無論廣狹,它們都代表了一種文明(文明)政治或謂規則政治的思維視野。孔子之述作損益與德禮政刑,包括了涵蓋天品德行、德治禮治與政刑之治的完備政教體系。
試以儒家經典《中庸》為例懂得所謂“兼體分用”。《中庸》援用了舜、周文武王、周公等圣王好事來印證中和之道。筆者曾指出,“這種證明方法,訴諸歷史上的典聚會場地范榜樣,而非一內在而絕對的超出權威,內里的歷史意識恰是此世文明超出維度的溯源性顯現,也奠基了此種文明形態在演進機理上的守舊基調。這種回溯返觀的守舊基調自己乃是文明積累演變的內在之義。”[15] 《中庸》第十九章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可以說,舜等圣王于文明傳統的長期演進中體認到了其最基礎精力,透過實踐弘揚于事業中,進一個步驟為全國配合體確立起維系更化的年夜經年夜法。這恰是“繼天立極”典范的要義地點。
另一面,我們又可看到《中庸》里皇帝與孔子兩種立法者腳色的張力。《中庸》第二十八章言:“非皇帝,不議禮,不軌教學場地制,不考文。明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第三十章又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六合之無不個人空間持載,無不覆幬瑜伽場地;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年夜德敦化。此六合之所以為年夜也”。
可以說,皇帝的管理事功是品德、時遇和權位相結合的高度復雜之實踐活動,需求命運或偶爾性的青睞;而孔子的政教價值在于將基原性的文明精力予以權威化體現,代表了更為恒常、更為持續的文明常道。如宋代經制學年夜儒薛季宣所言,“禮樂,圣人之事也;制禮作樂,皇帝之事也”[16],又如朱子于《中庸章句序》中明言:“自是以來,圣圣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17]。正表白了儒家擔當道統的最基礎法價值地點,與管理主體兼有統一意義次序而腳色各有分歧。三代的圣王權威可被視為原始政教典范的歷史表達,三代以后的圣人與王(后王時個人空間君)之分離則將此一典范中的內在次序張力進一個步驟凸顯出來,在宋儒以來的“道統—治統”話語中顯示出二元權威的契機[18]。
三、公共事理與共和霸道的演進
政教相維制的兼體分用機理,在次序主體上經由傳統的士正人、士年夜夫群體而得以構成一個穩定而積極的文明形態。這個文明腳色的精力特質,值得放活著界文明史的比較視野下,與古典以降的先知、祭司、國民、僧侶、騎士、知識分子相勘照。這里限于篇幅,不克不及展開論述。對于我共享空間們懂得中國文明的政教關系,士年夜夫傳統是政治、社會和文明史意義上的絕佳視角。
要言之,這一傳統重要脫胎于周代封建全國的政教體系,支撐了封建宗法制下貴族共治的禮樂文教系統。經由孔子儒家的創造性轉換,構成開放流動社會體中以德性文雅為內核的精英群體,繼承三代經典之文明規則而予以收拾提煉(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低小樹屋廉甜頭復禮為仁”),并積極參與到戰國以降的新次序構建中,最終在西漢武帝時奠基帝制全國的文明政治基礎。這一群體部門地接收了法家國家感性中的權要體制技藝,而以士正人為精力、文明和倫理成分的主干,在文明和政治配合體中充當文教—管理規則的發現者、繼承者、維系者與更換新的資料者。
我們可從如下維度窺見其政教價值:起首,他們支撐起了一個多層累進的管理結構,依據風俗、共識、慣例和禮法而確立起多中間的管理權威。秦漢以后,中國基層和平易近間社會的家族宗族、鄉約、保甲、書院、社倉、善堂等廣泛的組織和軌制創新都顯示出這種文教—管理的氣力。在國家當局層面,則構成與強力性權威共治的基礎格式;
其次,雖然歷經其他精力、學術思惟的挑戰和排擠,士年夜夫主體依據儒學勝利實現了幾次嚴重的理論變遷,接收道法、佛老,在管理技藝和形而上學/崇奉層面發展了本身,使之成為一個充滿內在豐富性的精力思惟傳統。同樣主要的是,這種汲取并未導致對于其它崇奉形態、尤其是宗教崇奉的壓制和驅逐,平易近眾甚至士人階層在精力層面構成儒學維系下的多元包涵格式。國家也發展出一個自基層上升至中心的國立教導體制,并積極奉行興文教化的政策;
第三,經由賢能優先的選舉軌制和較具自治精力的處所管理,士年夜夫階層比較能構成對于社會配合體的吸聚、流動效能,使得中國社會的當局(尤其是強力性管理權威)與社會諸組織之間維系一種較和諧的關系。士年夜夫進加入處之間,能夠經由政治和社會腳色的自若轉換,或許飾演二者之間的溝通紐帶,從而構成對于管理權威競爭和張力的有用均衡器。對于族群(夷夏)、階層(貴賤貧富)等社會分化氣力,重要依據德性規則進行整合凝集,這是中國文明傳統得以不斷擴展和異化的焦點機制;
第四,士年夜夫群體在國家政治中透過上述層級性、文教性、協調性的持續參與,催生出政教次序的制作機制。他們對于天道天命、風俗平易近情、祖宗成法的廣泛參照,出于經世實踐精力的穩健審慎,構成次序確立、維系和更換新的資料的活氣源泉。從次序機理上說,政權的成敗有賴于這一群體的德性與管理技藝,有賴于出于政教自覺或默契于政教精力的規則述作。這一點使其較具守舊教學場地維新之氣質,而對于同樣涌現于本身的年夜規模創制立法沖動堅持必定距離,更與現代中國經歷的激進反 TC:9spacepos273